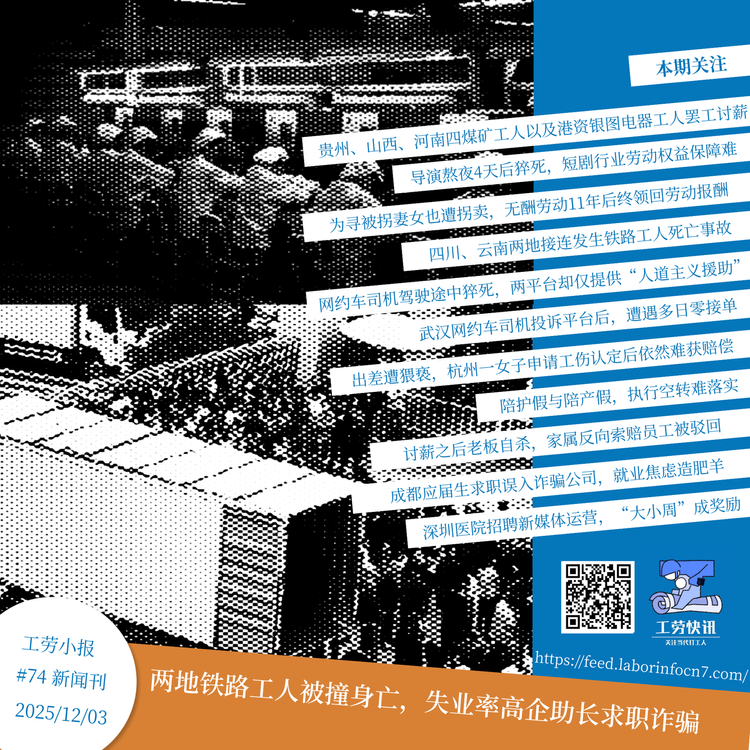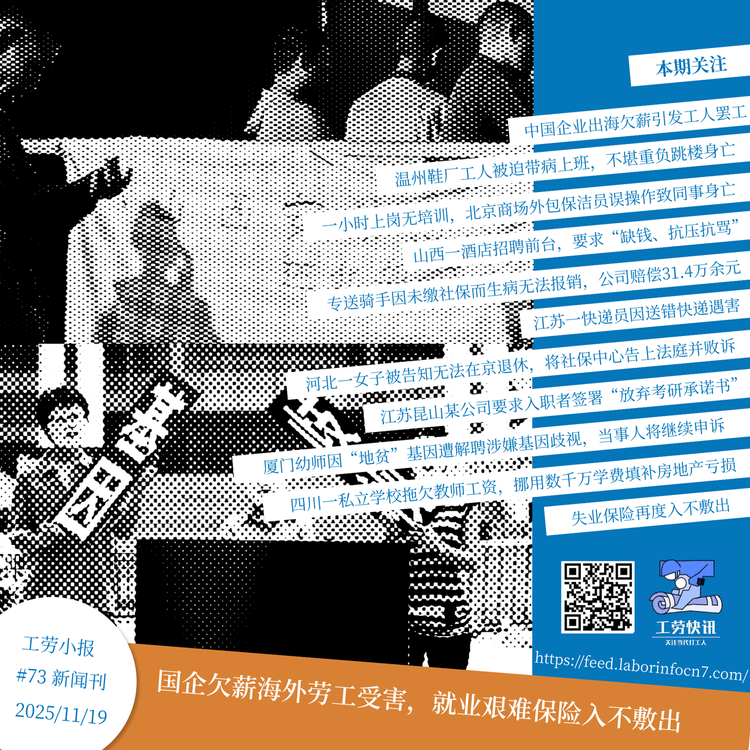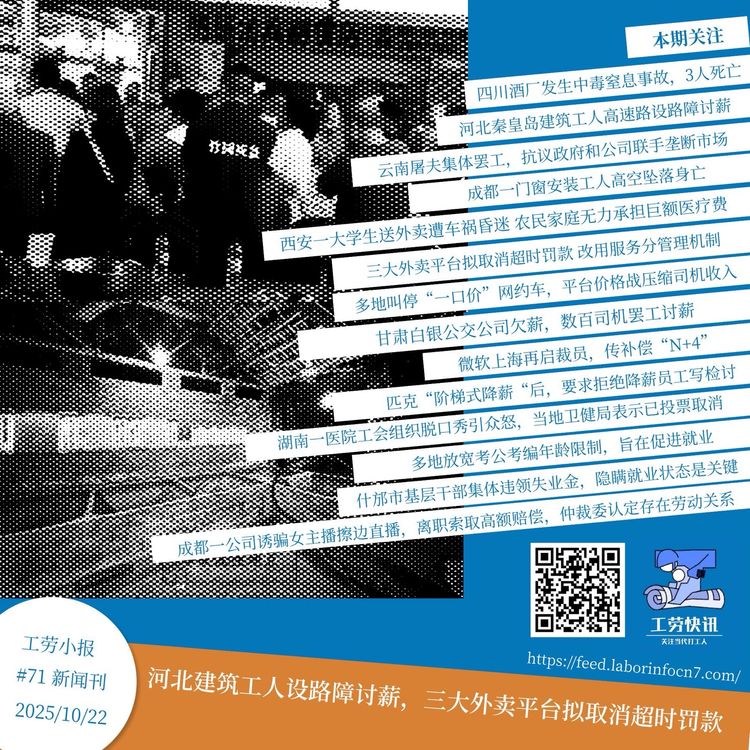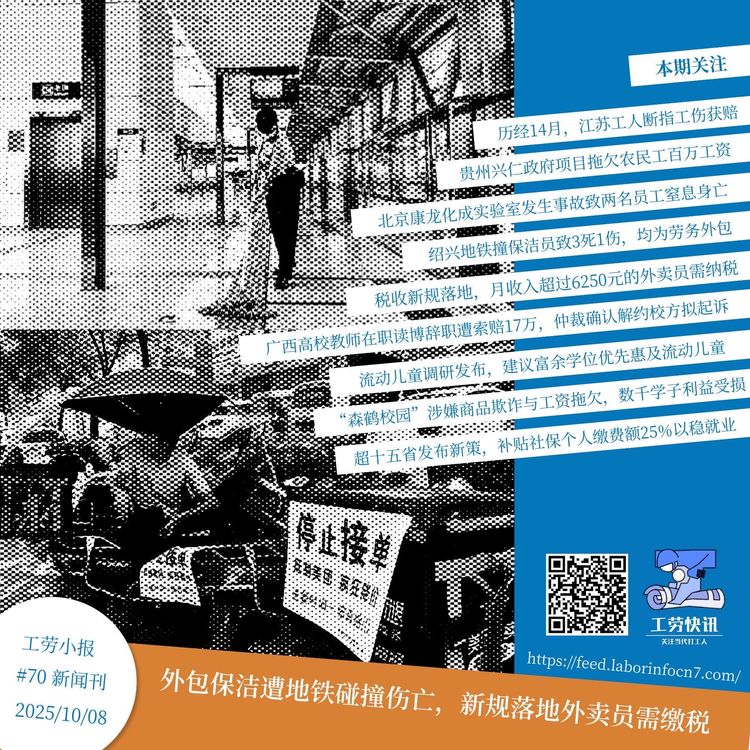付费工作的骗与真|工劳小报 #64 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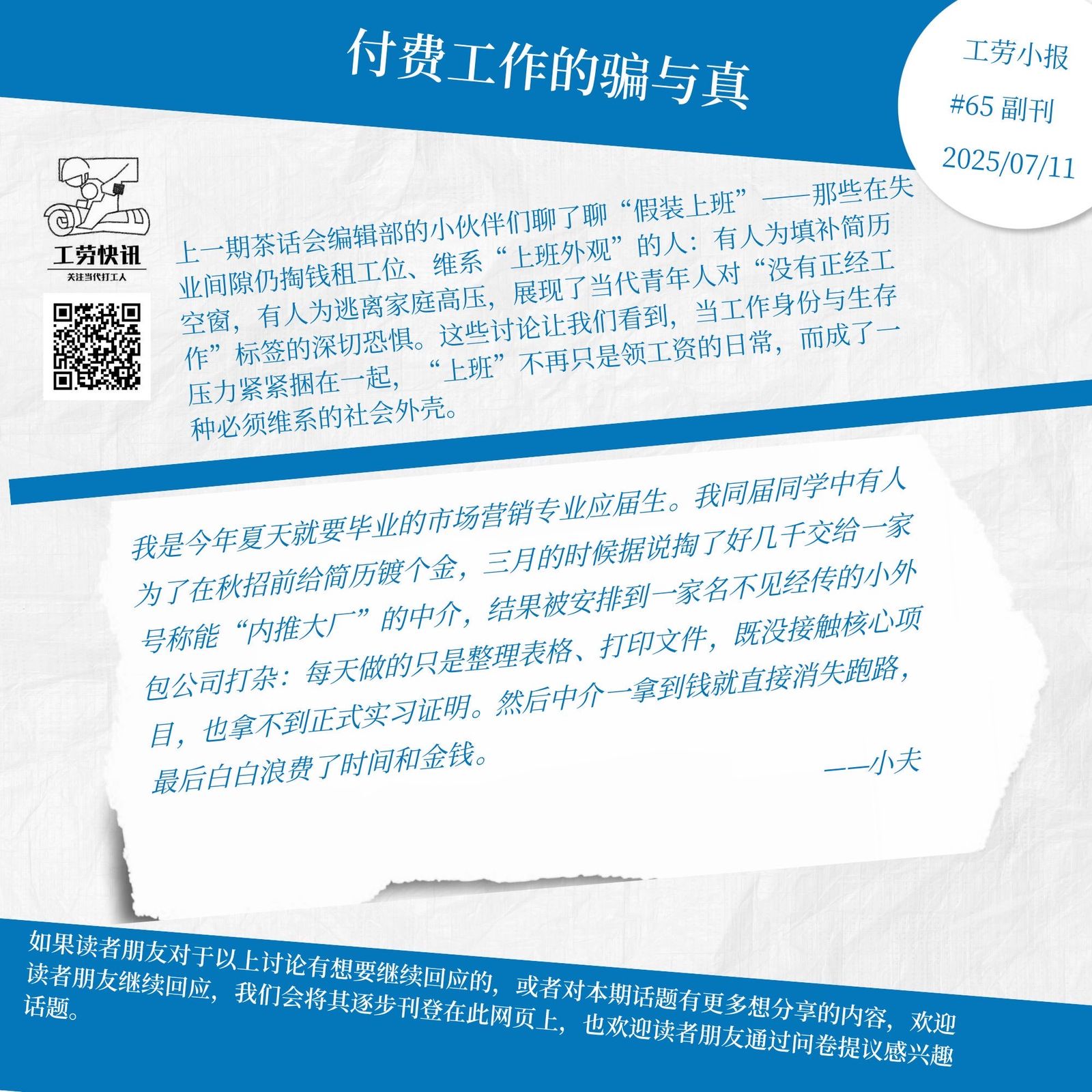
01 茶话会
付费工作的骗与真
上一期茶话会编辑部的小伙伴们聊了聊“假装上班”——那些在失业间隙仍掏钱租工位、维系“上班外观”的人:有人为填补简历空窗,有人为逃离家庭高压,展现了当代青年人对“没有正经工作”标签的深切恐惧。马乙己将其归为“付费实习”的延伸,指出交通、餐费、房租早已把实习与就业拉进“倒贴”模式;乌云则提醒我们,在“摇奶茶都要卡25岁”的就业洪流里,假装上班或许只是劳动者在低迷就业市场里的一座“临时避风港”。这些讨论让我们看到,当工作身份与生存压力紧紧捆在一起,“上班”不再只是领工资的日常,而成了一种必须维系的社会外壳。
读者小夫讲述了同学在大学毕业前经历付费实习骗局的安利,指出当前就业环境下乱象丛生的现状。
我是今年夏天就要毕业的市场营销专业应届生。我同届同学中有人为了在秋招前给简历镀个金,三月的时候据说掏了好几千交给一家号称能“内推大厂”的中介,结果被安排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外包公司打杂:每天做的只是整理表格、打印文件,既没接触核心项目,也拿不到正式实习证明。然后中介一拿到钱就直接消失跑路,最后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读者C也讲述了他选择“付费上班”的原因:
刚过完年回到公司,就看见裁撤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幸运的是最后拿着 N+1 赔偿走的。当时怕简历空窗,每天不停地在内耗,于是每天花 39 块去一个“假装上班公司”打卡:有桌子、Wi-Fi,还有一群同样被优化的陌生人。对我来说,这不是自欺,而是花钱给自己的作息,生活状态和求职节奏一个支撑点,让生活不至于分崩离析。
如果读者朋友对于以上讨论有想要继续回应的,或者对本期话题有更多想分享的内容,欢迎填写以下问卷,我们会将其逐步刊登在此网页上:https://forms.office.com/r/a1VpJWNirN ,也欢迎读者朋友通过问卷提议感兴趣话题。
02
法律与维权
以发高温费为由拒开空调,工厂被责令整改

2025年6月,上海某工厂车间化身“蒸笼”,工人反映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出现头晕中暑症状。面对工人开空调降温的诉求,该企业老板表示“高温费发了,空调别想了”,对劳动者的健康保障问题视若无睹。《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企业除发放高温津贴外,必须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条件。当工作场所温度超过33℃时必须采取有效降温措施;达到37℃以上时,室外作业必须停止,室内需将温度控制在35℃以下。经现场实测,劳动监察部门认定车间温度远超33℃,当场责令整改。发放高温津贴并不意味着可以替代实际的降温措施,高温津贴是补偿性权益,而提供安全作业环境是企业的强制性义务。阅读原文
便利店强制员工“买单”过期食品,劳动监察认定违法克扣

2025年6月,贵州贵阳观山湖区“凯辉便利店”被曝多项劳资矛盾。员工安女士反映,其4月无休加班超30小时,实发工资仅1267元(约定薪资3200元);另一员工杨女士工作51天到手2200元,扣除款项包括未卖完的烤肠、包子等过期食品,以及店内丢失的高价香烟。《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中列明:企业要求员工承担经济损失需有确凿证据证明其存在故意破坏或重大过失,且月扣款不得超过工资的20%并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6月10日,劳动监察部门调查人员当场表示,该店诸多举措涉嫌违法,但涉事店长仍声称“不认为违法”。6月12日,经劳动监察部门协调,安女士等三人获补发工资,其它劳资问题仍有待仲裁。阅读原文
03
资源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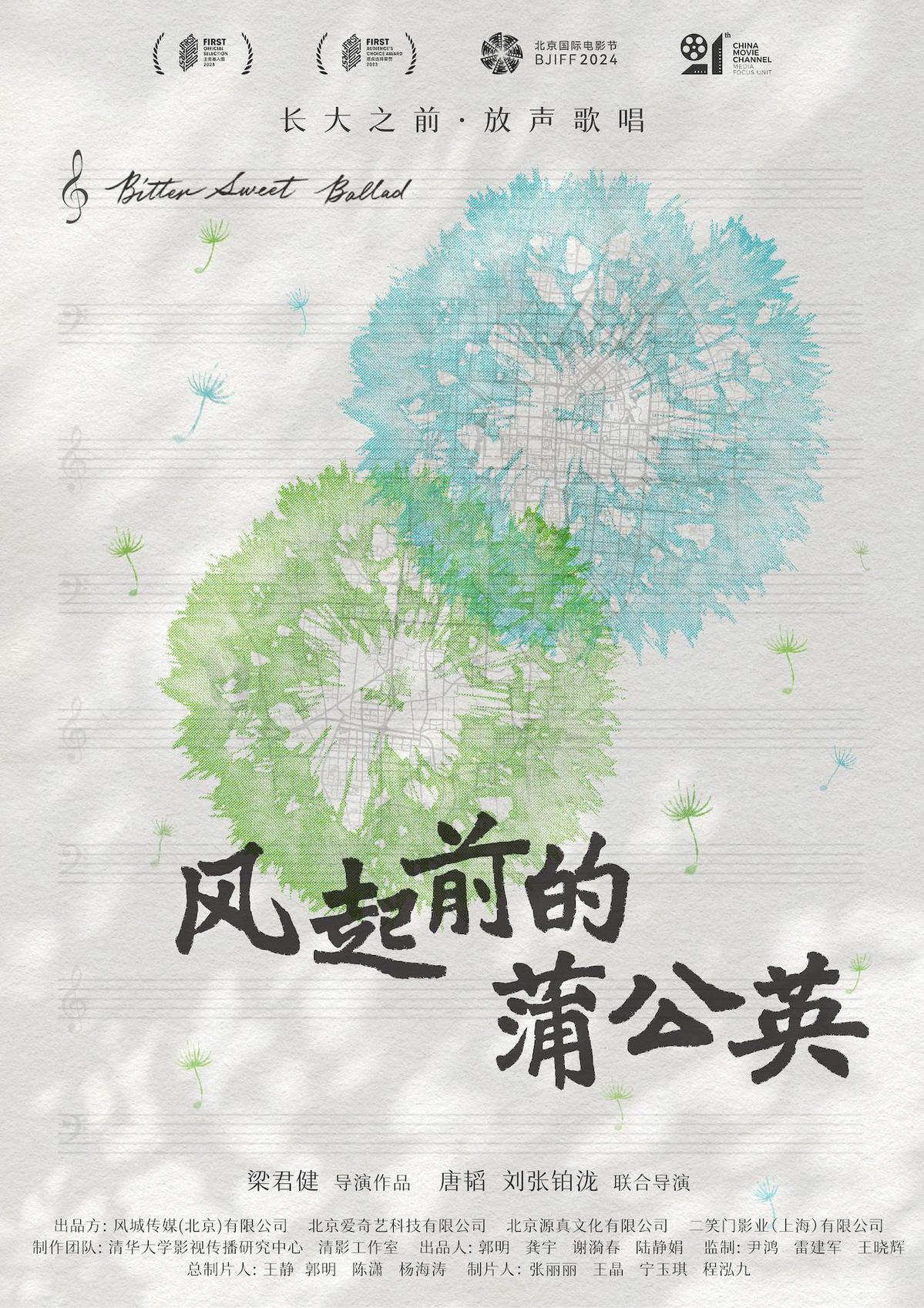
《风起前的蒲公英》由清华大学副教授梁君健执导,拍摄了北京蒲公英中学四位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与成长。这所学校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设立,几乎所有孩子都将在初二或初三回到户籍地中考。最初,导演带着一个明确的构想走进校园:拍一个“用音乐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但真正开始拍摄后,他意识到现实比叙事复杂得多。梁君健没有强行把他们套进“逆袭”的轨道,而是放弃宏大的主线,用两年时间,沉下去静静捕捉孩子们一次次搬家、离队、转学的过程。作为导演,他逐渐意识到:这些流动儿童不是“弱势群体”的符号,不是政策对象,而是在不同语境中努力成长和面对失落的普通孩子。ta们不是“为了成功而努力”,而是“在努力中逐渐明白,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
04
图片故事

茶百道新推出的荔枝饮品颇受好评,却累哭了各门店的员工。用于新品制备的荔枝并没有经过集中的预处理,往往需要店员每日手剥数十斤。
05
劳动碎语
三年后的今天,她在北京某上市公司上班,非技术岗,年薪27万,是52岁父亲在县城老家工作收入的三倍。但看似丰厚的薪酬被拆解成基础工资、绩效年终、分四年兑现的股权激励。直属领导一句“组里需要有人背低绩效”,就让她这个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年终奖直接腰折。
“工作日没有喘息的缝隙,22点后离开公司是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下班。”她的飞书签名常年挂着联系电话。哪怕高烧到浑身疼痛,确诊得了甲流,她也只敢请假半天,在医院拿完药,回到月租三千的合租房,晚上八点依旧要完成工作任务。“领导问能不能坚持,我哪敢说个‘不’字?”
来自《名校00后,不想整顿职场只想逃》
网友@猫猫库库回忆,自己的原生公司在新人融入方面有一套层层递进的规则。他入职后先是只被拉进了一个仅有三四人的小群,群里是他的直属领导与几位小组同事,除此之外没有把他拉入其他任何群长达大半年。他清楚地知道老员工们有另外的工作群、以及一个部门大群,因为其他人并不掩饰这一点,会直说“看xx群”“资料我发xx群”了。有时开会也不带他,只通知他最终结果。整个部门让他感受到一种“你还不够格融入”的窒息氛围,他一边愤怒于为什么所有人表现出一致对外的态度,时常与朋友吐槽这种职场文化的落后之处:
“大家难道不都是从新人过来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对待呢?”
来自《被第一份工作定型的打工人,把“原生职场创伤”捧上热搜》
竞业限制制度目前在中国呈泛滥的趋势,相关案件在最近五年攀升,直到2024年“爆炸”。以前,每年公开的案例才几十个,现在有的一家公司一年的案子就有上百个。尤其是互联网、新能源、智能驾驶、医药研发、制造行业,就城市和区域说,北上广深以及东南部地区最多。
一次,我去一家大公司处理案件,我代表劳动者这一方和公司律师谈和解。刚坐下,对方律师从电脑里调出一个Excel表,划到编号104号,找到我代理的案子。表格的每一栏写着诉讼金额和最终获得的款项,104号还只是整张表的中间位置。这种表格我只会在业务部门的财务报表里面看到。对方律师私下透露,今年法务部的创收还不错。我当时惊了,法务部和创收这俩词能联系在一起?
来自《困在百万违约金里的打工人》
父亲实在没招了,问我:“你们年轻人都怎么找工作的?”我掏出手机给他展示了几个求职软件,随后父亲在我的帮助下注册了其中的一个。但是登录进去后,父亲发现他感兴趣的绝大部分岗位都对年龄有要求,条件宽松一点的都要40岁以下,更多的把年龄限制卡在35岁,甚至30岁。“这是给你们年轻人用的。”在浏览了很久之后,父亲还是卸载了软件。
“记得刚回国的时候,投了200多份简历,最后只收到5个面试邀请。”林乔苦笑道,“最讽刺的是,现在的工作就是帮别人申请马来西亚学校。”她的工资条显示,扣除五险一金后,每月到手7200元,偶尔业绩好,加上提成才能勉强过万。但减掉在深圳租房、生活等必要花销,再减去3000元要用来还贷和补贴家用的钱,林乔自己手头就所剩无几了。
本期小报周期(2025/6/17 - 2025/6/30)
撰稿:汤圆、乌云、蓝水
编辑:马乙己
校对:水泥
在最后
以上是第64期工劳小报副刊的全部内容。我们正在探索将日常的工人资讯定期整理为 Newsletter,希望你可以来信([email protected])提出建议或加入成为志愿者,同时也请你多多分享给墙内的朋友们。点击下方按钮可以订阅和阅读往期内容。